如何看待人工智能?现在大致存在两种倾向,借用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话来说,一种是“好得很”,一种是“糟得很”。说人工智能好得很,是因为它是科技领域前所未有的大变革;认为它糟的很,则是因为人工智能的演进可能导致“超人”现象,霍金就曾认为,人工智能有可能会在将来的某一天赶上或超过人类,这项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很有可能导致人类的灭亡。在我看来,这两种看法都可能包含偏向。对人工智能这一个合理的态度可能是谨慎的乐观:一方面对它的发展前程要做充分肯定,另一方面对它可能的一些弊病要加以注意和防范。
最近,有一种现象需要引起我们注意,即文本的“复制”,其具体形式是以人工智能取代人,借助AI进行写作。前一阵复旦大学校庆的时候,便出现了很多完全雷同的贺词,数十所高校都以AI生成的文献作为贺信,其内容机械呆板,既没有创造性,也不合行文规范,这类文本的出现,可以说使斯文扫地:人工智能可能具有的负面作用,在此充分地显现。AI或人工智能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是人工的东西,人工智能与人的智慧之间有距离,人工智能毕竟是工具性的东西。我曾区分了一阶智慧和二阶智慧,前者(一阶智慧和)具有原创意义,后者(二阶智慧)则往往缺乏原创性。真正创造性、原创性东西则是人的创造,人工智能属于二阶智慧:如果离开人的赋予,包括大数据、算力、算法,人工智能就什么也不是。人工智能固然可以自我学习,孤立地看,其运算能力甚至超过人类,但其功能毕竟是有限的,归根到底,属于人类的赋予。比较而言,人的智慧则具有原创性,属于一阶智慧。对以上两个方面,需要加以区分。
从广义社会的层面来看,人工智能确乎开辟了一个新的虚拟世界,人与人之间交往也因此有了更多的方式和更广的空间。在虚拟空间中,自然的人可以与机器对话,不再局限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然而,这种新的现象也需要认真考虑。从一个方面来说,它使人交往的对象大大地扩展了,不再限定在一个区域或一定关系之中。但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不同于自然人。在与人工智能对象的交往中,人与人的情感沟通、美与艺术的交流、价值的共鸣、认知的共识都受到限定。同时,现实的交往过程涉及与人相关的各种意义、意味,对智能的机器来说这种意义和意味则基本上不存在,它对各种对象大致一视同仁、具有冷冰冰的性质。这种交往过程,显然有其限定,应当加以制约。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沉溺于手机、电脑世界之中,乐在其中,也就是说,主要囿于一个人机之间交往之中,没有扩展到人与人之间的广泛社会交往,这是需要避免的现象。社会的进一步的发展,应当在人与人之间交往中引入现实的社会关联,如果没有现实的人与人的沟通,便只能停留在由智能机器构成的冷冰冰的交往世界中,这对人类的演进过程显然具有消极意义。要而言之,除了理性的引导,人与人的往来不能仅仅限定于人机交流,而是需要注重现实的交往。从自然的、感性的层面,到社会性的维度,都不能离开现实的人。
人具有多方面的生命意义,包括精神层面的追求、人格的提升、不同的能力的发展,等等,这些方面往往不同于人工智能。同时,人的生命存在关乎感性规定,除了通过感性需要的满足以维系人的现实生命之外,人还通过自然繁殖来保证生命的延续,从智力发展演进看,这使理性能力无法离开人之“身”。相对于此,人工智能并非与自然之身相关,其运算能力也并不以“心”或“脑”为依托。人们谈及人工智能,对以上方面往往有所忽视,“非自然”意义上的“身”,往往未能进入他的视域。在自然之维,智能以心和意为内容,并与心意的展开无法分离。而在不同于自然的人工形态下,心与意常常游离于外:人工形态的智能,往往更多地以心意之外的逻辑运演为其特点,而不涉及自然层面的情感和体验。作为人工的产物,人工智能即使在某些方面超越人,但以上方面是它无法避免的。通过发展人的生命内涵和生命意义,人不仅将驾驭人工智能,而且能够使自身得到进一步的充实。人的目的性、人的尊严,都以非人工性为前提。对人工智能的规范,需要以此为原则。中国传统哲学肯定万物之中人为贵,这里的“人”主要即自然之人。人工智能应始终在人的控制之下,这是基于其非自然性。
理性的规定与目的性相互关联。人的理性能力与价值取向,是人不同于动物或其他存在的主要之点。人具有的理性能力表明,人是理性的存在;人所内含的价值取向则确认,人是目的性的对象。人工智能固然能够进行逻辑推论,然而,历史的发展则表明,人工智能的理性活动,是二阶性的,其作用过程,也离不开人的制约。人的价值与人作为自然存在的生命无法分离,人工智能则因其“人工性”,与人的自然生命始终存在距离:相对于人,人工智能无法摆脱物的形态。这一性质,从另一方面决定了其手段性。作为人的知识和认识能力的外化,人工智能的实际作用无法超越人的目的。事实上,人工智能的目的最终在于更有效地解决人类遇到的各类问题。以前面提到的“复制”来说,其意义不仅仅在于文本的生成,在人工智能中,它同时表现为自我学习的情况下的程序“复制”。为了避免其负面影响,需要在最初的程序(包括算法、算力)方面加以防范,因为这一类广义发复制,容易失控,当然,这里重要的是作预防性的规范。在“人工”的前提下,人工智能的一切所作所为,应该在人的控制之下,在此前提下复制,有助于免于导向消极结果。
总体上,关键的问题在于肯定人的创造性和目的性,应当始终坚持只有人是目的、唯有人才具有创造性。需要以这样的观点来制约人工智能的发展,引导其未来的趋向。从人是目的这个角度来说,早期儒学已提出仁道观念,其内在涵义是肯定人具有内在的价值。《论语》中的著名记载:马厩失火,孔子闻知,马上急切地问“伤人乎”,但“不问马”。其中的缘由在于,马是为人所用的工具,而人本身即目的。这是就目的性规定而言,从理性的创造过程来看,则不能把一些东西都归之于人工智能的生成,需要始终肯定人的原创性。可以看到,肯定人是目的和人的创造性品格,将人工智能作为服务于人和社会治理的手段,并以此规范相关活动,这是未来可能的一个前景。
(本文为7月19日召开的《分析哲学》创刊15周年纪念会议发言,会议主题为“智能社会与期刊发展”)
转载请注明来自夏犹清装修公司,本文标题:《杨国荣︱人工智能与社会运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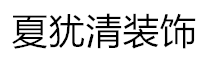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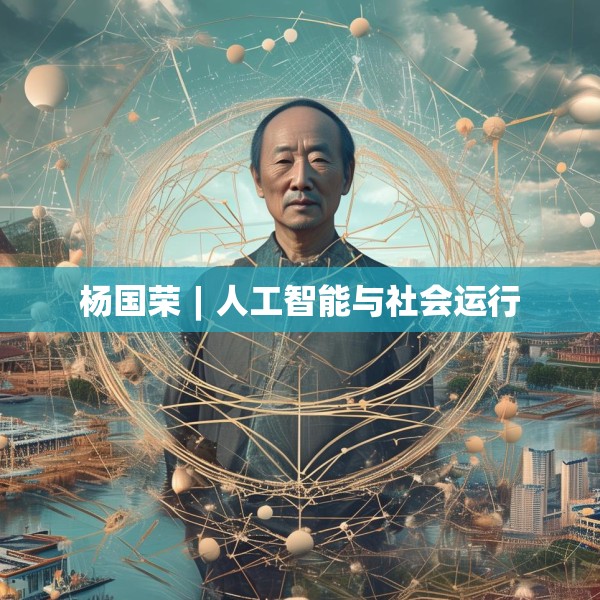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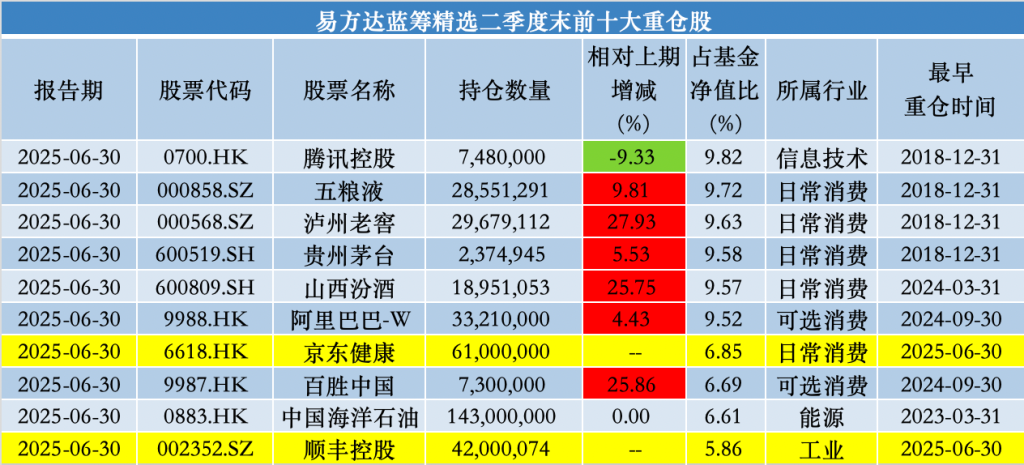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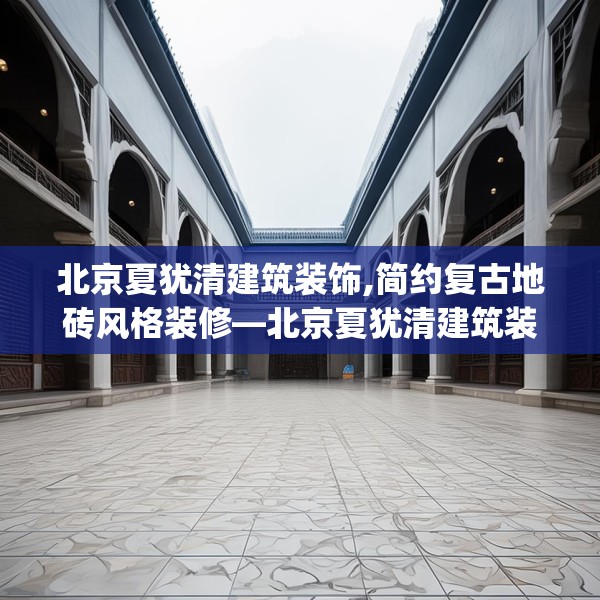



 京ICP备2025104030号-3
京ICP备2025104030号-3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