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李丽丽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破产法研究中心研究员
8月26日,在厦门市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厦门经济特区个人破产保护条例》(以下简称《厦门个破保护条例》)表决通过,并拟于11月1日施行。这是继深圳之后,我国第二部个人破产地方性法规,标志着厦门在综合改革试点中率先探索个人破产制度。
对《厦门个破保护条例》条分缕析,不难发现其身上具有《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以下简称《深圳个破条例》)影子,但又多了一些很多与市场经济适配性更强的因素。比如,《厦门个破保护条例》虽也规定了辅导咨询前置,但同时也规定了债务人可以在咨询辅导时申请与债权人进行债务清理,这无疑增加了灵活性,不但可以避免大量的债务清理工作一下子涌入本就不堪重负的法院,也可以避免咨询辅导沦为“程序空转”。
从债务门槛上,《深圳个破条例》规定债权人申请时需满足单独或合计持有到期债权50万元以上的金额门槛,《厦门个破保护条例》则采用“上一年度人均可支配收入五倍”的动态标准;从豁免财产上,前者豁免财产上限20万元,包含生活必需品、职业工具等,禁止包含奢侈品;后者的上限为上一年度人均可支配收入三倍(动态调整),新增宠物等具有精神陪伴的财产,允许置换豁免财产,标准更灵活,更注重人文关怀,更具科学性与适应性,这无疑更加贴近“债务”与市场经济的本质:在确保诚信的基础上,只有保护债务人基于生存与发展的需求,才能释放出更大的生产力;只有债务人释放出更大的生产力,债权人才能获得最大程度的清偿。
个人破产保护,从来不是保护负债的债务人,而是保护债务人对未来发展的预期,保护债权人对债务人诚信、市场诚信的期待,保护每一个个体都能在债务的世界中,有尊严地活着。
个人破产中的“免责”:并非等同于“欠债可以不还钱”
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人类与动物一样,“逃避”是遇到危险时刻在基因里的自我保护手段,甚至在兵家的三十六计中,也视“走”为“上计”。但不同的是,人类对于社群关系纽带具有更强烈的需求,切断所有社会联系的逃避一般都是因为需要面对巨大的法律责任。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公众将“个人破产”等同于“欠债可以不还钱”,对个人破产制度所存有这样的误解,并不能苛责大众——在中国人民的传统理念里,“欠债还钱”本就是“天经地义”,甚至“父债子偿”也是彰显诚信文化的因素。但是,正是这种高压的传统理念与舆论下,很多债务人选择了逃避——轻者删除好友、断联失联;重者人间蒸发、人去楼空,抑或留着一家老小收拾烂摊子;更有甚者,从高处一跃而下,不管下面是水泥地还是河湖。这种对待债权债务关系的态度,并不能给债权人带来更为实际的清偿。如果将债权债务形容一条绳的话,极限拉扯的最后必定是绳断事毁。
最近,有一条新闻让普通民众的心理破防,说某地的首例“个人破产”案,负债214万,只还3.2万。这类标题的表述,其实具有比较大的误导性,容易让大众简单地将214万=3.2万,这种数字之间的落差,一度被认为是法院鼓励欠债不还或少还。但实际上,这两个数字背后还有一个完整的故事,债务人“承诺,该方案履行完毕之日起六年内,若其家庭年收入超过12万元,超过部分的50%将用于清偿全体债权人未受清偿的债务”。在这个案件中,以3.2万元的首期偿债金额,撬动的是六年时间内债务人的发展性,而债权人的清偿,恰恰源于债务人的未来发展。
著名的破产法泰斗王欣新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指出,债务人申请重整程序,要有稳定的可预期收入用于清偿债务。经协商,债权人与债务人可以在重整计划中作出减免债务的约定。债务人要按照重整计划及时向债权人还债,这对债务人和债权人来说是双赢的。因为在重整程序中,债务人可以获得清偿债务的喘息机会,并适当减轻债务,而债权人则可能获得高于破产清算程序的受偿率。
个人破产的核心:喘口气、继续前行
王欣新教授所说的“喘息机会”,意味着个人及其家庭的发展与前行。如果长期关注强制执行领域,就无法忽视一个动态的数字,截至2025年8月30日,已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为8,463,468人,若以限高人数为失信人员人数的1.5-2倍(限制法定代表人和1-2名股东)保守估算,约为1700万人,而实际人数,可能远远高于这一数字。这近2000万人的背后,是2000万个家庭。如以每个家庭3个人计算,受到影响的人数则更多。
中国人民大学破产法研究中心主任徐阳光教授在接受采访时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 “有钱不还,归执行管;确实没钱,归破产管。我们现在要做的制度设计,需要考虑法院如何识别被执行人是有能力而不愿履行,还是确实丧失清偿能力,并据此将债务人分别导入执行程序或破产程序中”。徐阳光教授同时也提到,“债务人不进入破产程序,也会出现转移、隐匿财产、拒不执行的情况。进入破产程序,恰好有手段查清其是否转移了财产,并进行逃废债调查,实施相应惩戒。”
因此,个人破产制度如设计得当、适用得当,非但不会成为债务人逃废债的工具,反而会成为防止逃废债的利器。因为,与破产配套的制度是监督与核查。比如,在深圳,多部门共同编织了一张信息核查监督网。深圳中院可以整合法院、市场监管、不动产登记中心、人民银行、公安等部门数据资源,建立跨部门核查平台,由专业机构对个人破产信息进行核查,必要时对债务人的清偿能力进行科学评估,让隐匿的财产无所遁形。《厦门个破保护条例》也规定,法院、破产事务管理机构、管理人依法监督和查看债务人财产变动情况、收入和支出情况、对限制性措施和法定义务遵守情况等诚信状况,如出现隐匿、转移、毁损财产的情况,轻则丧失获得减免债务的机会,重则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包括刑事责任。
个人破产制度探索的三块试验田: 江浙深个人债务清理的“中国化”方案
2020年8月,全国首部个人破产法规《深圳个破条例》通过,对于持续关注个人破产领域的专家来说,《深圳个破条例》无疑是我国破产制度尤其是个人破产制度发展的里程碑,甚至就连长期关注中国破产制度发展的国外学者,也将其与我国台湾地区的个人破产制度进行比较研究,并认为《深圳个破条例》代表着中国未来个人破产制度发展的方向。
与深圳不同的是,江浙地区也有类似于个人破产制度的实践,称为“与个人破产制度功能相当试点”、“个人债务清理(类个人破产)”,这是一种在执行程序与破产程序衔接的实践探索。执破衔接机制是个人破产制度设计的关键环节,是甄选“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的关键环节。让可执行的归执行,让可破产的归破产,这直接关系“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能否成功纾解债务,同时也影响司法资源的优化配置及司法效率。
从深圳和江浙的制度运行实践看,各地区均对执破衔接或执破融合制度的设计上予以充分重视。从制度设计角度观之,三地试点都在探索个人破产的“中国化”方案,以适应我国国情。江苏的试点以“与个人破产制度功能相当”为核心,主要关注执行程序中的诚信被执行人。通过债务和解与免责考察,帮助这些被执行人“退出执行”。这一路径实际上是将破产理念融入执行终本程序,为“执行不能”的案件提供了一条退出通道。相比之下,浙江模式以“个人债务集中清理”为核心,更加强调债务清理和债权人之间的协商。通过设置双重表决规则和引入公职管理人等机制,更多地体现了执行程序与破产程序的衔接,旨在弥合两者之间的功能隔阂。
但就立法层面,深圳的试点颇具突破性。作为全国首个地方性个人破产立法,《深圳个破条例》涵盖了清算、重整及和解三种程序,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制度框架。该条例不仅为“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提供了重生的机会,还通过严格的财产调查和固定的考察期等规则,防止破产制度的滥用。
尽管我们目前无法预测《厦门个破保护条例》实施后的情况,但只有各地越来越多的差异化探索,方能构成个人破产制度发展的“中国式实验”,方能为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个人破产法律体系提供了多维度的参考。我们有理由期待,在不久的将来,一个既符合国际破产法发展趋势,又具有中国特色,还能够彰显社会诚信的个人破产制度体系将逐步形成,最终形成一个兼顾公平与效率、平衡债权人保护与诚信债务人再生的现代化个人债务处理机制。
(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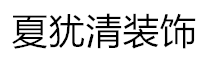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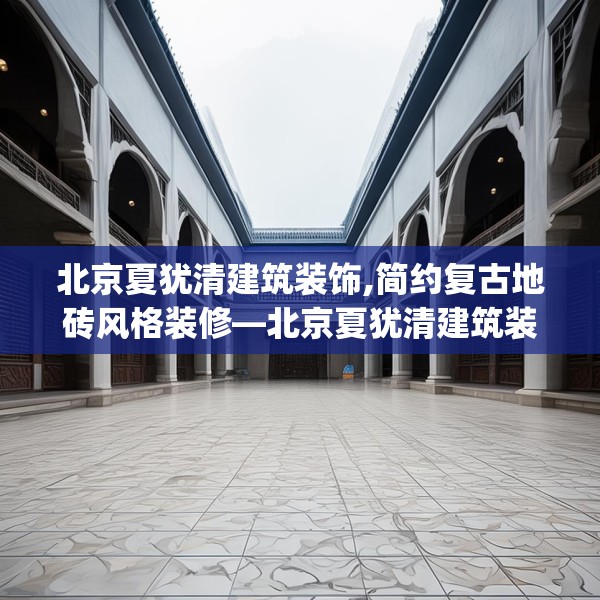



 京ICP备2025104030号-3
京ICP备2025104030号-3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